隨著資本經營領域的發展創新,并購重組日益成為市場資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由此產生的并購重組稅收爭議也不斷出現,對現有的稅收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在案情和法理分析的基礎上,重點研討了并購重組實務中爭議較大的個人所得稅納稅時點與計稅依據問題并提出了可行性政策改進建議。
基本案情
張某曾于2015年創建某小型科技公司B,持有B公司100%股權,初始投資成本1000萬元。因發展前景被看好,2017年5月15日B公司被A上市公司100%收購。作為對價,張某取得A公司定向增發的股票500萬股,并于當日辦理股權變更手續,2017年5月15日A公司股票的收盤價為10元/ 股。
按照個人所得稅的相關規定,張某在該并購重組過程中應當確認財產轉讓所得4000萬元(500×10-1000=4000),并需繳納個人所得稅800萬元(4000×20%=800)。但該筆并購協議中約定張某取得的該500萬股股票有2年的禁售期,即一段時間的“轉讓不自由”。張某無法將手中的股票變現,缺乏現金流繳納個人所得稅,于是按照《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41號)第三條的規定1向稅務機關依法申請了遞延五年納稅。由于股市低迷,2019年5月15日股票解禁日 A公司股票當天收盤價僅為2元/股,且股價繼續下滑態勢明顯。張某于2019年5月29日以1.5元的價格忍痛拋售全部500萬股股票,取得收入750萬元。2019年6月16日,張某收到稅務機關通知,要求他繳納2017年5月并購重組業務中申請遞延的個人所得稅至少800萬元。但張某認為自己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應認定在2019年5月29日拋售股票真正取得現金的當天,真實凈收益為拋售股票收入750萬元減除股權初始成本1000萬元,不僅沒有產生應稅所得,且虧損了250萬元,卻被要求繳納800萬元稅款,實不合理,并拒不繳納。稅務機關發出《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告知張某,如有異議,根據《稅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條,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2019年7月5日張某依法提供了納稅擔保后,向上級稅務機關提請行政復議。上級稅務機關受理復議后,于2019年7月20日作出維持原稅務機關征收行為的復議決定。張某不服,又將稅務機關訴訟至當地人民法院,法院在審理后,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維持稅務機關復議決定的判決。
爭議焦點
在上述訴訟案中,稅企雙方產生的爭議焦點主要圍繞并購重組中個人納稅人取得股權支付的納稅時點與計稅依據如何進行要素確定這一問題。其中納稅時點,即納稅義務的發生時間是核心爭議點,計稅依據直接根據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當日的股票市場價值減除計稅成本可計算得出。對雙方的爭議焦點分析如下。
稅務機關認為,按照現有政策文件規定,并購重組中個人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和計稅依據應該按照取得股權支付日進行要素確認。依據有二:
-
一是根據財稅〔2015〕41號文件第二條 :“個人以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應于非貨幣性資產轉讓、取得被投資企業股權時,確認非貨幣性資產轉讓收入的實現。”本案中張某于2017年5月已經取得被投資企業A公司股權,應當按照財稅〔2015〕41號文件確認原B公司股權轉讓所得4000 萬元。
-
二是根據《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 (試行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67號,以下簡稱《辦法》)第二十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繳義務人、納稅人應當依法在次月15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一)受讓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二)股權轉讓協議已簽訂生效的;……”
本案中A公司已于 2017年5月支付全部對價股票且股權轉讓協議已生效,張某應當按照《辦法》確認股權轉讓所得并申報納稅。由于 2017年5月張某取得的支付對價中全部為A公司股權,現金不足以繳納全部應納稅所得,根據財稅〔2015〕41號文件第四條“個人以非貨幣性資產投資交易過程中取得現金補價的,現金部分應優先用于繳稅;現金不足以繳納的部分,可分期繳納。個人在分期繳稅期間轉讓其持有的上述全部或部分股權,并取得現金收入的,該現金收入應優先用于繳納尚未繳清的稅款”,稅務機關同意了張某的延期納稅申請,但是納稅義務發生時間與計稅依據4000萬元在2017年5月已經確定。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之間市場價格波動發生的4250萬元股票貶值虧損,屬于市場性風險,應由張某自行承擔。
張某及其代理律師認為,本案中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和計稅依據應調整至張某所取得A公司股票再次轉讓日(即2019年5月29日)進行要素確認。《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收回轉讓的股權征收個人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5〕130號)第一條規定 :“股權轉讓合同履行完畢、 股權已作變更登記,且所得已經實現的,轉讓人取得的股權轉讓收入應當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張某認為該條款中的“所得已經實現”是納稅的前提條件,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的發生不僅要求具備合同履行完畢以及股權變更登記的條件,還要求具備“所得已經實現”的實質要件。本案中張某的所得是股票,且由于股票存在“禁售期”和價格波動,張某實質意義上的所得“未真正”實現或者所得是“未確定”的,不符合“所得已經實現”的實質要件。因此,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應推遲至2019年5月29日拋售股票當天,并按照當日成交價計算原B公司股權實際轉讓收入750萬元,并最終確認股權轉讓虧損250萬元。
法理分析
稅收公平是指國家征稅應使各個納稅人的稅負與其負擔能力相適應,并使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平衡。衡量稅收公平原則的標準有兩個,即受益原則和負擔能力原則。由于股權轉讓的納稅義務與受益性的直接關聯度不強,本案中我們重點關注負擔能力原則,即根據納稅人的納稅能力來判斷其應納稅額的多少和稅負公平與否,納稅能力強者即應多納稅,反之則相反。財稅〔2015〕41號文件通過在交易環節鎖定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和計稅依據保證了稅款計算的確定性和國家稅源的穩定性。但是,該文件中的有些條款過于剛性,在資本市場整體低迷的情況下,給市場主體的并購重組帶來了不確定性,不利于推動市場主體之間的資源整合和資本要素的充分流動。如果可以通過調整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和計稅依據給重組主體以“定心丸”,不僅體現了負擔能力原則,更符合市場主體的心理預期。當然,全盤接受納稅人的訴求也存在問題。在實際情況中,部分個人持有重組支付對價的股票長期不出售,并將股票用于向金融機構質押以獲取資金變現進行其他投資和消費,這種行為不僅是對稅收公平原則的背棄,更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國家稅款征收的遙遙無期。
啟示及建議
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深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愈發顯著。并購重組作為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重要手段,深受企業歡迎。因并購重組通常通過股權(票)支付以節約收購方的現金流并達到并購雙方利益捆綁的商業目的,所以通常對符合特定條件的并購重組行為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暫不征稅,從而有利推動了市場并購重組和優化要素配置的積極性。但是,當并購重組涉及到自然人股東時,相關稅收爭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主體的并購重組決策。綜合考量上述三種立法原則的貫徹,建議立法部門應結合當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和企業訴求,充分推動生產要素流動和產能整合,激發市場活力,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改進完善并購重組中的個人所得稅政策。具體可以考慮以下兩種稅制優化方案。
將并購重組中被收購方獲得的股權支付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延遲到股票解禁可轉讓時點,并根據可轉讓時點當日股票收盤市價計算應納稅額。計算公式為:
應納稅所得額=本批次解禁股票可轉讓當日市價×本批次解禁股票可轉讓份數-被收購方股權投資成本×(本批次解禁股票可轉讓份數÷被收購方獲取的禁售股票總份數)
股票解禁時即確定納稅義務和計稅依據,后續是否轉讓股票、何時轉讓股票可由納稅人自行決定,不受政策因素干擾。該方案結合交易條件重新確認納稅義務的發生時點,不僅充分考慮了自然人所持股票禁售期間股市價格波動對實際轉讓所得的影響,充分權衡了納稅人的負擔能力,體現了公平原則,而且納稅義務時間和計稅依據固定明確,更加保障了相對穩定的稅源,貫徹了稅收效率原則。
將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延遲到實際轉讓時點,并在確定計稅依據時綜合考慮銷售當日股價與解禁日股價。自然人收到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支付對價的股票,具有一定的限售條件或禁售期,其特性更像《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票增值權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5 號)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權激勵有關個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61號)中的限制性股票,即股票授予對象只有在滿足特定年限或業績目標符合計劃規定條件的,才可以出售限制性股票并從中獲益。故筆者認為,可以借鑒限制性股票轉讓的計稅方法,以個人受讓的有特定“禁售期”的股票在股票登記日的股票市價和本批次解禁股票當日市價的平均價格計算應稅收入,并據此確認應納稅所得額。同時約定個人解禁股票的時間一般不得超過股票登記日起五年,超過五年的,按照滿五年當日的股票市價視同解禁確定納稅義務和計稅依據,以保障國家相對穩定的稅源,繼續貫徹效率原則。計算公式為:
應納稅所得額=(股權重組日股票市價+本批次解禁股票當日市價)÷2×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數-被收購方股權投資成本×(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數÷被收購方獲取的禁售股票總份數)
該方案結合最終股票解禁時間重新確認了納稅義務發生時點,平衡了國家和納稅人雙方的權利。最大的優點是不僅考慮到了自然人所持股票禁售期間股市價格波動對實際轉讓所得的影響,而且考慮到了自然人在持有禁售股票期間,因可以通過股票質押獲得相應資金的支配權而理應承擔部分股票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最大程度體現了實質公平原則。
此外,在完善稅制的同時還需考慮配套稅收征管制度的優化。客觀地說,與在股權登記日確認納稅義務和征稅相比較,遞延納稅稅制的優化的確會“犧牲”一部分效率,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稅收債權后期執行力的減弱和喪失。因此,建議立法部門和稅務部門進一步加強稅收征管能力建設,提升征管質效,重點關注以下三方面的配套措施 :
-
一是加強與政策優化配套的征管制度安排,明確自然人納稅人享受稅收優惠的流程以及需要承擔的相關法律責任,明確征管部門的管理職責。
-
二是充分運用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治理優勢,對股權并購和股票解禁等并購重組相關市場操作開展跟蹤監控,強化并購重組個人所得稅遞延納稅相關的后續風險管理。
-
三是深化協同共治,加強與其他行政部門的信息互換、信用互認和管理互助,推進個人納稅信用體系建設,讓相關的政策最大程度發揮出社會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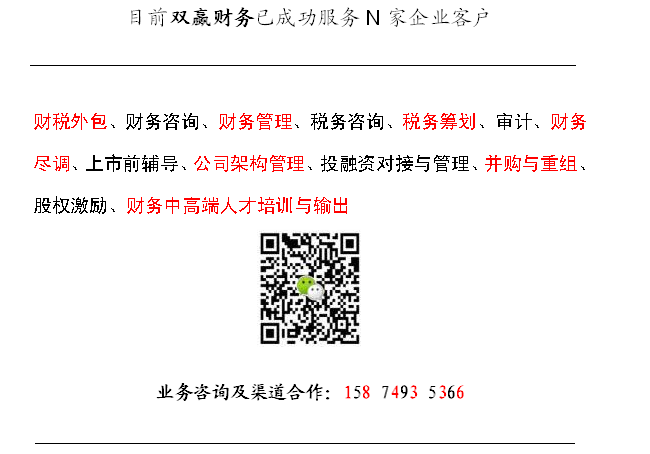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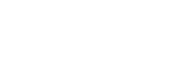
 湘公網安備 43010202001085號
湘公網安備 4301020200108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