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A房地產公司的財務人員接到了主管稅務局的通知,要求自查說明2017年度是否少繳納了企業所得稅。該公司財務人員一頭霧水:2017年度的企業所得稅緣何會少繳呢?稅務機關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A公司2017年度主要開發建設一住宅項目,共40棟住宅樓,2017年度企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為5400萬元,已如數繳納。2017年度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過后,主管稅務局使用“房地產全流程AI稅收風險管理系統”,對企業匯算清繳的結果進行了全面復核。
“房地產全流程AI稅收風險管理系統”是一個基于大數據分析的AI系統,覆蓋房地產企業從拿地到銷售的全過程,全面采集管理證照信息、納稅申報信息、發票信息、會計報表信息、銷售備案信息等,能夠智能化進行大數據計算、風險特征比對、稅務大數據管理,自動識別企業是否存在稅務風險,并做出稅務風險排查方向提示。
主管稅務局采用該智能稅務系統進行檢查時,發現A公司2017年度城鎮土地使用稅申報繳納數據存在異常。借助該智能稅務系統,稅務人員拿到了一張清晰明了的圖表:2017年A公司城鎮土地使用稅第一季度申報繳納100萬元,第二季度申報繳納100萬元,第三季度申報繳納60萬元,第四季度申報繳納15萬元,逐季減少幅度較大。“房地產全流程AI稅收風險管理系統”提示稅務人員:A公司可能少計了應納稅所得額,可能存在少繳企業所得稅的情況。
A公司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申報繳納信息與企業所得稅有何關系?“房地產全流程AI稅收風險管理系統”據此判斷該公司可能少計企業所得稅的理由是否成立呢?
根據國家相關政策規定,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范圍內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和個人均應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稅。
一般來講,計算方法為:應納城鎮土地使用稅額=開發初期應稅土地總面積×城鎮土地使用稅單位稅額標準×(1-累計售出房屋建筑面積/房屋建筑總面積)÷繳納期限。
根據上述公式,累計售出房屋建筑面積是計算應納城鎮土地使用稅額的關鍵。在房屋建筑總面積確定的情況下,累計售出房屋建筑面積越大,應納城鎮土地使用稅額就越小。與此同時,累計售出房屋建筑面積越大,應該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額也應該越大。基于這一邏輯關系,“房地產全流程AI稅收風險管理系統”提示,在2017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A公司很可能大量交付了開發產品,但并未如實計算完工開發產品應納稅所得額。
經過約談,A公司財務人員承認,由于項目工程成本最終結算未完成,不能準確結算會計成本,也未如數結轉營業收入,不過在2017年度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中,已根據《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企業所得稅處理辦法》(國稅發〔2009〕31號,以下簡稱31號文件)的規定,將銷售未完工開發產品取得的收入和預計毛利額,計入了當期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
A公司2017年企業所得稅年度納稅申報表附表顯示:銷售未完工產品的收入為145500萬元,毛利率為15%,則銷售未完工產品預計毛利額為145500×15%=21825萬元。根據其他相關數據資料核算,計算無誤。但是,A公司忽略了31號文件第九條的另一規定:開發產品完工后,企業應及時結算其計稅成本并計算此前銷售收入的實際毛利額,同時將其實際毛利額與其對應的預計毛利額之間的差額,計入當年度企業本項目與其他項目合并計算的應納稅所得額。
根據31號文件第三條規定,開發產品已開始投入使用,應視為已經完工。在進行2017年度所得稅匯算清繳時,A公司已經有大量開發產品“交付”,投入使用,據此可判斷其開發產品已經完工,因此就應按31號文件第九條規定,結算銷售收入的實際毛利額與對應的預計毛利額之間的差額,計入完工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根據已結轉的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判斷,該項目開發產品實際毛利率估計為30%。
由此推論,假設A公司開發產品會計成本等于計稅成本,2017年度可能少計應納稅所得額145500×(30%-15%)=21825萬元,涉及企業所得稅預計21825×25%=5456.25萬元。
最終,A公司財務人員對此邏輯分析結果認可,同意補充申報2017年度企業所得稅年度納稅申報表并補繳企業所得稅和滯納金。
城鎮土地使用稅與企業所得稅兩個稅種看似無關,但稅收風險管理系統不是拘泥于某一稅種的稅務風險識別,而是由此及彼,順“稅”摸“稅”。納稅人應通過不同稅種之間內在的稅收政策邏輯關系計算分析,做到稅務風險早識別、早預警。
當前,“互聯網+稅務”智能化應用發展很快,納稅人更應提高稅收遵從度,根據稅收政策規范納稅處理,切實注意各稅種之間邏輯關系,不能犯“顧此失彼”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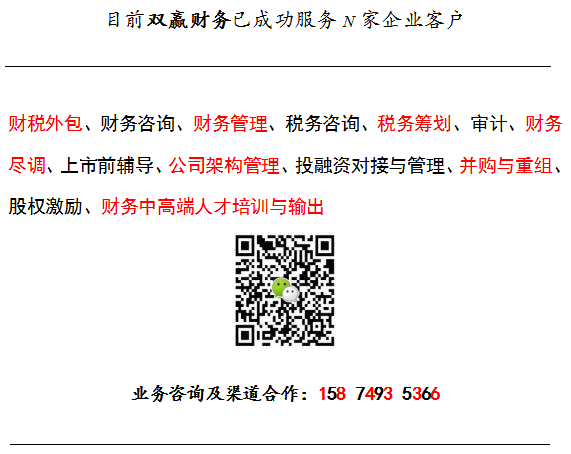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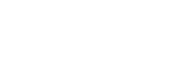
 湘公網安備 43010202001085號
湘公網安備 43010202001085號